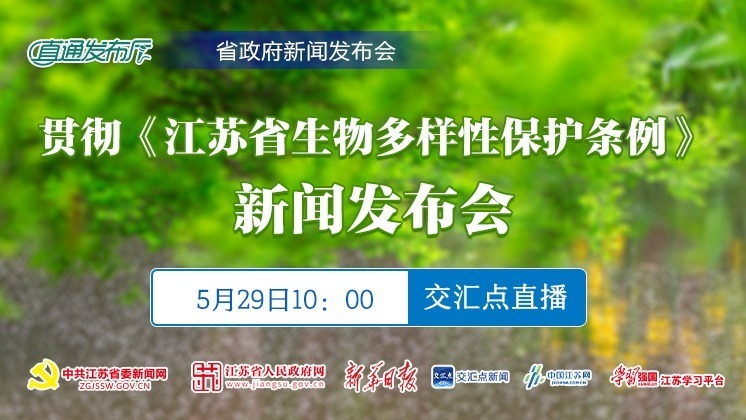在昆山某处考古工地见到何文竞时,他正和几名技工一起,用管子把探方里的雨水抽出。前一天下过雨,雨水将探方填满,使得考古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工地上泥泞得很,何文竞的皮鞋经常陷在泥里。他已经在这处工地上驻扎了5个多月,皮肤晒得黝黑。“我们干考古的,天天风吹日晒,大多皮肤黑。”何文竞说。他撸起T恤的袖子,露出一小截较白的皮肤,与裸露在外的黑皮肤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何文竞从事考古工作的第六个年头。干这一行,全然是兴趣所致。“我本科学的是地球物理勘探,在中国石油干过几年,因为喜欢考古,就辞职读了安徽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何文竞告诉记者,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考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如愿成为一名考古人。
6年里,何文竞在所里待着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考古工地上。考古是个慢活儿,他在工地附近租间房,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同时,这份工作也挺寂寞的,得长年累月地和泥土、器物、骸骨“相处”,如果没有兴趣,很难坚持下去。“我干这一行还挺开心的,虽然每天都得在工地上做一些重复性的挖掘工作,但没有两个墓葬是完全一样的,常常会有惊喜。”何文竞说,他始终觉得考古工作是有趣且充满意义的,“考古是现代人了解历史最直观的途径。”
怀揣着这样的热忱,何文竞参与了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的3个勘探项目、3个调查项目以及17个发掘项目。其中,太仓樊村泾遗址、东山岭下窑具遗址、虎丘路新村土墩均为近年来苏州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新发现,为研究元代龙泉窑瓷器的出口、六朝时期苏州的窑业情况以及六朝时期高等级墓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虎丘路新村土墩的墓葬挖掘工作长达1年多。1年多时间里,我住在工地旁边的出租屋里,每天早出晚归。”何文竞说,墓葬的规模很大,大墓旁有个坍塌的侧室,得先把砖块全部清走才能开始工作,“清理完砖块再筛土,要慢慢地、细细地筛,因为有些物件特别小。”那一次,何文竞和同事筛出了若干小金片和小金珠,最小的金片直径仅1毫米。除了筛土,常用的方法还有水洗,但无论哪一种方法,都要求考古工作者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最终,虎丘路新村土墩共发现7个文化层、1个西汉时期器物坑、1个西汉时期土坑墓、1处三国孙吴时期碎砖堆积面、8座砖室墓(三国孙吴时期砖室墓4座,六朝时期砖室墓1座,宋代砖室墓3座),出土文物219件组。
在田野考古的实践中,何文竞承受着风吹与日晒。“夏天被太阳晒得疼,冬天的情形就更糟糕了。”他回忆,2016年发掘太仓樊村泾遗址时正值冬天,下大雪,“只能穿得厚一点,外面罩一件雨衣,脚上套两双袜子,咬着牙把工作做完。中午在工地上吃饭,捧盒饭的手冻得直哆嗦,饭菜一会儿就冷了。”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何文竞也凭着对考古的热爱与激情撑了下来。对他而言,考古是拨开时间的尘埃探寻历史的“回声”,是揭开岁月的面具找到过去的真相。他愿意一直为这项事业而奋斗。(记者 王敏悦 实习生 吴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