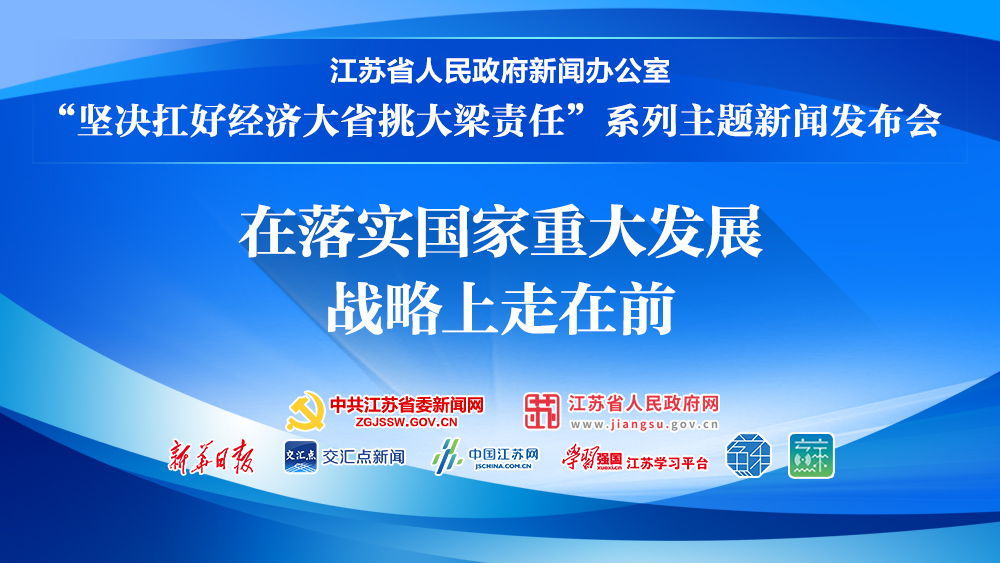古琴,又称“七弦琴”,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弹拨乐器,也是中华民族器乐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古琴与中国文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流传至今的古琴渗透了音乐之外很多的人文思想。

虞山琴派传承人至今依然抚琴而奏
古城常熟,与古琴也有着特殊的渊源。明代邑人吴讷有诗曰:“虞城枕山麓,七水流如弦。昔人肇嘉名,千古称琴川。”常熟别称琴川,盖取七弦琴水之意——古代常熟城内有七条溪流,形似古琴七弦,横向排列,汇入南北向的主河道。取琴川之别名,只是描摹山川形胜的造化巧合而已。真正要说到常熟与古琴的渊源,那么诞生于此的虞山琴派就不得不提。琴音缭绕,千年文化积累,江南小镇与古琴相生相伴,渊源深矣。
明代常熟地方琴人很多,并受来常熟教书授艺的浙派徐门第三代传人徐梦吉(号晓山)之影响。此外,徐晓山之后,常熟又出现了著名琴家陈爱桐,虞山琴派创始人严天池、徐青山,均师承其子陈星源。严天池吸收了京师名家沈音(字太韶,浙江绍兴人)的长处,创立了虞山琴派。

虞山派古琴艺术馆(资料图)
自明代严天池开山立宗之后的三四百年间,虞山派古琴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堂奧,登堂入室探幽者除前述外,其载于志乘者还有:季图瓛(莲涧),得常熟支塘人谭清(冰仲)传其指法,于《胡笳四序》尤为擅长;顾恪(文徵)、赵元素、王道行、程伯垣、丁耀夫等,皆以琴名。入清以后,又有陈翼(友石)、陈珉(山民)、单嘉豪得虞山正派。由此可见,虞山琴派一脉传承,人才辈出。
“清微澹远,博大和平”是“虞山琴派”的风格特征。“虞山琴派”于明代万历间由严天池始创,之后风行天下,追随者众多,其代表作《松弦馆琴谱》成为《四库全书》所收的唯一一部明代琴谱,荣耀至极,一直被琴界奉为正宗。那时期,粗制滥造的琴谱充斥于市,一些琴人热衷于逐音填配文辞,或为一些并无音乐性的诗词配音。尽管其中有少数优秀之作,但也被湮没在大量低劣作品之中。严天池疾呼:“琴之妙,发于性灵,通于政教,感人动物,分刚柔而辨兴替,又不尽在文而在声。何者?试使人诵诗,雄者未必指发,而肃者未必敛容,唯鼓琴,则宫角分而清浊别,郁勃宣而德意通,欲为之平,躁为之释。盖声音之道,微妙圆通,本于文而不尽于文,声固精于文也。”《松弦馆琴谱》也正是那时严天池为力匡时弊所编订之作。
严天池所倡“清微澹远”的琴风与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党争失意而追求退隐山林之趣,可谓不谋而合。这种宁静、闲逸乃至出世的思想在艺术审美上表现为一种简约、恬淡、清虚的风格。《松弦馆琴谱》诸多琴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顺应自然,追求隐逸超世、返璞归真的思想。通过琴曲,后人能够透过宁静、冲远、淡泊的山水田园,感受到其中的“禅趣”与“玄思”,想必才是真正参透了严天池所留“瑰宝”。悠悠琴曲之中,仿佛能够看到一代琴宗严天池衣冠整肃,盥手焚香,移座琴案,调弦取音。在一方山水庭院之中,但见落指发声泠然,犹如冰玉之漱幽涧,顿时,四座寂静,琴韵悠悠,心驰神往。

虞山琴派艺术馆内展览(资料图)
虞山琴派独特的表现手法和深邃的美学思想,不但深刻影响了国内的广陵派、诸城派的产生和发展,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古琴艺术的流行和发展。公元1677年,虞山派琴人东皋禅师东渡日本。东皋禅师在日19年,大传华夏琴道,对日本的文化、艺术、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被誉为日本“近世琴学之祖”。近300年来,古琴艺术在日本广泛流传开来,演奏古琴也成为日本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今虞社”等组织的传承,虞山琴派生生不息,直至当代。20世纪80年代,由翁瘦苍发起组织虞山琴社,其一直担任社长,从事古琴艺术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培养了不少古琴人才。他所弹琴曲萧疏淡雅,指法刚劲,很好地继承发扬了虞山琴派古风。翁瘦苍之后,又有其学生朱晞,于2009年5月当选为中国古琴学会会长,其风格在虞山琴派的传统基因上更具气象,一派灵机。在江南虞山脚下的这座城市,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不息,琴派后人承载了古人所留之瑰宝,同时也启发后人以传统文化为傲,不忘根源。

虞山琴派传人朱晞现场弹奏(资料图)
古琴悠悠,琴川雅韵,虞山琴派的古琴做到了宁静致远,注入了中国文化的灵魂。七弦上发出的太古声音恰似流水,在喧嚣之中漂洗着人们的灵魂,博大和平,源远流长。所谓琴川,在水一方。虞城青山下,琴人不止,琴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