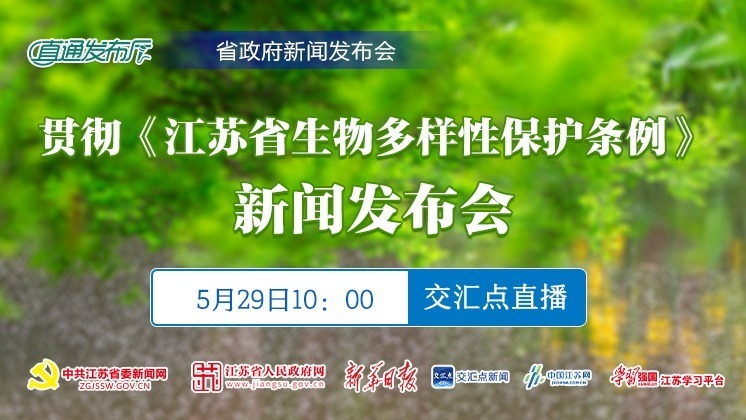秦少游诗曰:“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这里的“苏徐州”指的是苏东坡。公元1077—1079年,苏东坡在徐州当太守两年左右,不仅留下很多德政,还留下了300多篇诗文。公元1082年他才自称东坡,后世也叫他苏东坡居多,而“苏徐州”,是在他自称东坡之前另一个最典型的代称。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的开始可谓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苏轼极其果敢冷静地带领徐州百姓成功抵抗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之后,徐州便修筑了一座“黄楼”,既是取“土能克水”之意,又是对苏轼于危急中挺身而出、无私勇敢地拯救古城壮举的感谢。元丰元年(1078)9月,当黄楼建成之日,苏轼登楼欢饮并作《九日黄楼作》一首。在诗中,苏轼面对新筑的黄楼充满无限感慨,一面回忆起前年洪水袭城时可怖的景象以及自己和众人忙于抗灾无暇赏花饮酒的紧张情形;一面表达了自己为刚刚落成的黄楼成为古城新景而异常欢快的兴奋之情。
除了抗洪,苏轼还在元丰元年的春夏之交率领徐州百姓抗击了一场极为严重的旱灾。“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面对严峻的旱情,苏轼忧心忡忡,却又无计可施,率属下同去徐州城东的石潭祈雨。许是被苏轼的诚意所感,徐州普降甘霖。在面对同僚道贺时,苏轼不仅没有贪功,反而保持了一如既往地淡然:“君看大熟岁,风雨占十五。天地本无功,祈禳何足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在密州未能完成和弟弟苏辙团圆的心愿,却意外地在徐州赴任的途中得到了实现。兄弟情深打动了苏辙的长官张安国,特许苏辙陪伴苏轼共赴彭城。兄弟二人得以在颍州之别后的第六年共度中秋,喜出望外的苏轼提笔又书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有句:“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在徐州,苏轼还结交了许多徐州当地的朋友,比如自号云龙山人的张天骥。张天骥是一位才学俱佳却选择遗世独立的隐士,对比自己深陷世事、烦恼不断的生活,张山人成为了苏轼笔下理想君子的寄托。著名的《放鹤亭记》便是苏轼在与张天骥交往过程中书写的一篇文学经典。
徐州阶段的苏轼虽然饱受变法派的批评和攻击,却依然对于国事保持着强烈关注。
首先是奖掖后进,提举贤才。苏轼一生都有爱才惜才的美名,这固然有他早年被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欧阳修等人的提携经历有关,也和北宋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有关。元丰元年苏轼曾在黄楼主办了一场“鹿鸣宴”,这是在乡举考试放榜次日宴请主考﹑执事人员及新举人的仪式。在这场宴席上,苏轼创作了《徐州鹿鸣燕赋诗叙》,鲜明地表达自己对于人才选拔的态度。
其次,体恤弱势群体,整饬法令制度。《乞医疗病囚状》作于元丰二年正月,彰显了苏轼悲天悯人的个性。对于被囚禁的罪犯,寻常人往往是避之不及,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苏轼却以一种超越常人的境界提出囚犯的医疗救治权。
(本文编辑整理自微信公众号“方志江苏”)